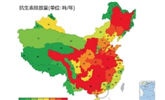蓝莓讲述:我把父亲送进拘留所
2016年09月23日 14:12
来源:凤凰时尚
作者:蓝莓
高老师是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为了这篇稿件,他先后来找我两次,诚恳地接受我的采访。回首往事,这位儒雅的汉子几度落泪。

高老师是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为了这篇稿件,他先后来找我两次,诚恳地接受我的采访。回首往事,这位儒雅的汉子几度落泪。


高老师是一位退休中学校长,为了这篇稿件,他先后来找我两次,诚恳地接受我的采访。回首往事,这位儒雅的汉子几度落泪。其实,关于他在那个特殊时期被审问的部分,他原稿中所写的和他对我所叙述的要比我在这个稿件中展示的内容残酷得多,也细致得多。但我考虑到这毕竟是一篇忏悔文字,而所谓忏悔就是他自己做错了什么、给当事人造成了什么危害,所以还是多挖掘一下他自己的错吧。高老师最终同意了我的意见。
一位先哲说过,人生的道路上有很多开关,轻轻一按,便把人带进黑暗或光明两种境界。高老师说,这话他信,因为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疯狂年月,他就曾不止一次地触碰过一个这样的开关。想到老陈头的死,特别是想到他可怜的父亲被他亲手送进了拘留所,罪恶感就在他的五脏六腑内燃烧。往事就像沉重的铅块,长时间地堵在他的心口,搬挪不动,愈堵愈沉。
 陈老头因言获罪,田间地头草木皆兵
陈老头因言获罪,田间地头草木皆兵1966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像熊熊烈火一样,烧遍神州大地。我的家乡虽地处偏远的科尔沁草原最南端,也照样在劫难逃。
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生产队的院子里,一群人天南海北地闲侃。我们几个小学生在他们中间打闹嬉耍时,听见80多岁的陈福元老头说:“现在这国家就能吹牛,说一分钟就能造一架飞机。要是那么快飞机早多得把天遮上了。”
那年我12岁,念小学五年级。“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老师就常对我们讲,发现坏人坏事要及时报告。课文里也有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就是地主去生产队偷辣椒,他发现了,在搏斗中被地主掐死了。老师以此进行教育,说一定要警惕阶级敌人搞破坏,比如反动的话、反动标语,等等……
第二天,我们几个把陈福元的话报告给老师,老师表扬我们警惕性高,有觉悟,并指导我们写了《万炮齐轰陈福元》的大字报。大字报由我执笔,用毛笔写在一张大白纸上。
我们把大字报贴到生产队队部的墙上。当时墙上已经有了一些大字报,都是大人们写的。老陈头也看到了写他的大字报,他总上生产队溜达,但他不识字。有人对他说:“老陈头,你看,写大字报了,批你的,你有麻烦了。”
陈福元知道后,吓得整天惴惴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不敢出门了。
大队领导根据陈福元的“反动”言论,决定开批斗会。会场设在大队部,会场内四周的墙壁上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
在一片吆喝声中,陈福元被押进会场,大队副主任邵××问:“陈福元,你为什么说国家吹牛?你为什么反对国家、污辱国家?你这个老中农,国家哪点亏待你了?”陈福元哆哆嗦嗦地站在地中央,呆滞的目光环视着四周,似乎在寻找什么援助。邵××大声呵斥着:“你装什么,快说!”
坐在炕沿上的老社员李老太太语气柔和地说:“ 老爷子, 你就说吧!”陈福元望着李老太太说:“这国家是好,家里有啥都不怕丢。要是在早年,家里养的骡子、马……”还没等陈福元说完,邵××就气冲冲地打断了他的话:“你还没忘你那点家产。你这是怀念旧社会,真是罪该万死!”陈福元连忙低下头……
批斗会开始,邵××讲话。大意是:陈福元说国家吹牛,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问题十分严重,我们准备上报公安局,让陈福元做好思想准备。陈福元吓得脸色煞白,汗珠子浸了出来,两腿一软,瘫倒在地上。
批斗会宣布结束。陈福元被其儿子搀回了家。三天后,陈福元将自己吊死在村外的一棵大树上。
陈福元死后的20多天,正是铲地的时节。那个年代讲以阶级斗争为纲,讲政治挂帅,每天家家都要做“早请示,晚汇报”。而且,劳动期间休息时要集中政治学习。
一下下午3点歇气时,人们按规定围坐地头儿开始政治学习。生产队团支书高声朗读《红旗杂志》中的一篇文章。突然,不知是谁带来的小狗一声尖叫窜出人群。“你真不是人!”地主子弟张××边骂边用手擦烟袋嘴儿。人们一阵哄笑。
“怎么回事?”生产队长赵××厉声地问。张××手指着李××说:“他把我的烟袋嘴儿往狗嘴里插!”“那你就大喊大叫?你不知道是在政治学习吗?有事不能学习结束再说吗?”“他祸害人还不能说吗?”“你还不服气?你还敢顶嘴?今天政治学习不学了,现在批斗张××!”
队长令张××站着,并宣布了张××的罪行———破坏政治学习。
接着,他开始讲话:“张××在政治学习时大叫大骂是什么性质的问题呢?是阶级斗争问题。不把这样的坏分子批倒批臭,阶级斗争就不会停止……树欲动而风不止,‘反动派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
队长口若悬河,引经据典,滔滔不绝地讲着,从国内形势讲到国际形势,讲得唾沫飞溅,天黑日落。半天时间就这样过去了。
关于老陈头的死,我当时没啥感觉,没觉得与自己有多大关系。
后来我高中毕业回到农村参加生产队劳动,大伙儿唠嗑儿时提起了这件事,说老陈头死得太不值得,咋因为那点事就吊死了呢?我有个屯亲,我叫他关姐夫,他对我说:“青春,你这小子作孽了。老陈头咋死的?就是你们几个小子写大字报给逼死的。”当时我还和关姐夫争辩两句,后来我也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愧对老陈头。
 父亲一巴掌惹下冲天大祸
父亲一巴掌惹下冲天大祸如果说,老陈头的死我是始作俑者,而我父亲的悲剧,则是我一手造成的。
我父亲的事, 发生在我15岁那年。1970年7月末,刚放暑假,我与堂兄在树趟子里打了三码子草(十码子草可装满一马车)。那时在草原上打草公社有时间规定,一般在8月10日左右开始打草,叫“开甸子”。我们哥儿俩没上草原里打。
一天中午,我家正在吃午饭,住在前院的我大娘来到我家,吵吵嚷嚷地说:“这程×也太欺负人了,两个孩子打点柴火要给没收。老五(我父亲排行),咱们不能容他,跟他干!”
我父亲脾气暴,听我大娘这么一说,把筷子“啪”地摔在桌子上,起身就向生产队走去。见到程×,父亲问:“你为啥没收我们打的柴火?”
程×说:“谁批准你们打柴火了?”父亲说:“我们又没上草原里打,在树趟子里打点烧柴犯毛病吗?”程×说:“你说这些没用,一会儿就派车去拉。”父亲说:“陈老六打一大车草藏在林场为啥不没收?”程ד腾”地站起来说:“你管不着,就TMD没收你的!”父亲说:“你嘴里干净点,跟谁TMD呢?”程×说:“就跟你!”父亲大怒,扬手打了他一脖溜。接着他俩厮打在一起。
这时,我舅妈(我舅妈是程×的妹妹) 背着孩子来到生产队,冲着程×哭哭啼啼地说:“哥啊,你别跟人家打了,人家都研究了,打算打死你。”
这话无疑于火上浇油,程×指着父亲破口大骂:“ 高老五, 我看你咋打死我?你不打死我,你就不姓高!”
这时,程×的哥哥手举割草的扇刀从屋子里冲出来,扑向父亲。与此同时,上来几个人夺下扇刀把他推回屋里,一场血案被制止了。
父亲这一巴掌惹下了冲天大祸。第二天,程×住进了公社医院。传出话说,程×左手拇指被父亲打坏了,伸不开。在程×住院的第三天,母亲去医院探望了程×。我们屯距公社医院10里路,当时母亲生我小弟弟还未满月,身体非常虚弱,10里路歇了五次。到医院母亲说了很多拜年话,请程×原谅父亲。程×答应两天后就出院。
结果过了半个月,程×也没出院。听人说,程×是受了大队副主任邵××的影响。邵××背后指使有原因,他和程×、陈老六是亲戚,我们和邵家又有家族矛盾,邵××抓住这个机会官报私仇。他向公社报了案,公社派来了调查组,父亲被送进了公社办的学习班。
学习班的主要对象是“地、富、反、坏、右”分子,父亲被定为“坏分子”。在学习班里除了劳动、学习,还要被批斗,父亲被游斗了全公社的17个大队。一天,批斗组来到与我们
相邻的大队,我骑着自行车偷着去看批斗会,心里惦记父亲啊!被批斗的共有4个人,他们站在拖拉机的车厢上,每个人脖子上挂着一米长的牌子。父亲的牌子上写着“坏分子高××”。父亲低着头,两臂下垂。七月的中午,火辣辣的太阳悬在天空中,强烈的光线刺得人难以睁眼,我看见父亲涨红的脸上汗珠直淌。
批斗开始,他们罗列了父亲的多条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说父亲好逸恶劳,不愿参加生产队劳动,经常谎称有病不出工,一年出工不到300天。我知道,父亲患有慢性肝炎,体弱乏力,繁重的农活父亲每天都是咬着牙挺着,感冒了就吃止痛药顶一下,从来舍不得耽误一个工,11口之家要靠他一个人挣工分养活啊!二是说父亲好打架斗殴,是屯里的害群之马。从我记事起,从未看到父亲和谁吵过嘴,打过仗。父亲是个老实善良的人,屯里谁有活求到他,他宁可放下自己的活也要高兴地去帮忙。父亲和屯里人相处和睦,人们都说“高老五是个好人”。然而,批判稿里竟然把父亲说成品质恶劣、道德败坏的社会渣滓……
批判稿一念完,群情激愤。有人大叫:“揍他!”有人大骂,骂的话粗俗腌臜,不堪入耳。还有人将土坷垃和烂西红柿投向父亲。父亲就来回躲,可他也躲不过来啊!我的心像刀扎一样难受,泪水泉涌一般夺眶而出。我在心里呼喊:“爹啊,你太冤了!”
专案组软硬兼施,我作了假证25天后,父亲从学习班被放了回来。父亲被办了学习班,我们以为没事了, 可程×仍在医院里不出来,说不光是手不好使,还患了神经官能症。父亲的问题升级了。公社这回又派来了一个专案组,公安助理也来了。
专案组主要是来挖这件事的动机,即是否研究打死程×。专案组把主攻对象定在我身上。晚8点把我传到大队部。队部的炕上放着一张炕桌,炕里盘腿坐着一个40岁左右的胖男人,他就是公社的公安助理。炕沿边上坐着大队治保主任。大队副主任邵××坐在靠墙的八仙桌旁。
他们三人个个紧绷着脸,看起来事态严重。这样的场面我哪见过啊,吓得我心“ 咚咚”直跳,脑袋“ 嗡嗡”作响。我不由得双手下垂,僵直地站在地中间。
过了大约3分钟,邵××开口说道:“你爹的案子没完,问题严重,弄不好得判刑。现在就看你的态度,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要是如实交代,就能减轻你爹的罪行。”我问:“交代什么啊?”邵××说:“你们研究要打死程×的,是怎么研究的?”我说:“我们根本没研究。”
“你不要嘴硬,说不说?”见我低头不语,炕里的公安助理突然将手枪“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不说,我明天就把你送县公安局!”
他这一举动,吓得我浑身一颤,眼泪在眼圈里打转。
他们审了我一晚上,夜里10点钟才放我回家, 让我回去好好想想,明天晚8点再来大队部。我受了委屈,脚一迈进家门,泪水一下子流了出来。但我不能哭出声,任凭苦涩的泪水在脸上流淌,进屋后忙洗脸。父亲问我:“ 他们问你什么了?打没打你?”我说:“问研究没研究打死程×,我说没研究;他们也没打我……”
第二天晚上,他们让我站在地中央,双腿并拢,手贴裤线不准动,说一动就是承认研究打死程×了。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不动太难挺了,我不停地扫视他们,希望找个机会动一动。谁知他们吸着烟,喝着茶,眼光却不离我的身。从晚上8点站到夜里12点,站得我腰酸腿疼,天旋地转。“你说不说?”公安助理说话了。我说:“没有的事我说什么?”“你不是不交代吗?今天就到这儿,明天晚上继续来站着。”
接下来,一连站了三个晚上。那些天,无论怎么晚,父母总是等着我回来。他们观察我的神态,问这问那,我总是假装无所谓的样子。
审问到第7天晚上,邵××一反常态,笑呵呵地让我坐在炕边上,用手抚摸着我的头:“青春啊,你这孩子,咋这么犟呢?看你这几天都瘦了,其实你要是说了也没多大事。你想啊,你们不是没把程×打死吗?你爹不就打程×一巴掌吗?顶多给你爹再到县里办一次学习班,顶多一个月就回来了。”我问:“你说话算数吗?”公安助理接过话说:“我代表公社,说话算数,你写个交代材料就完事了。”
说实在的,当时我对他们的承诺也是半信半疑。但这么多天的审问, 我实在是挺不住了。一是困。每天半夜三更才能回家睡觉,第二天在课堂上打不起一点精神,天天遭老师批评,我又不能跟老师说明情况,真是苦不堪言。二是累。不但身累,心更累,那比山还大的压力让我喘不过气来,我太想尽快结束这种难熬的日子了。另外, 我还抱着一种侥幸心理: 我亲姑父当时是我们县法院的副院长,我即使作了假证明,他们也不会把我爹怎么样。
于是,我违心地在一张白纸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爹和我大娘研究打死程×”,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写完交代材料,我怀着复杂的心情离开了大队部。
 父亲被抓,家里生活陷入困境
父亲被抓,家里生活陷入困境一个月后的一天下午,屯里突然来了一辆吉普车。车停在我家院子后,从车上下来两个公安。公安向父亲宣布逮捕令。见此情景,我惊呆了,傻眼了,悔不该写交代材料,是我害了父亲!
父亲被戴上手铐,推进吉普车。父亲上车后两眼凝视着我们,好像有话要说,但一声鸣笛,吉普车开走了。站了一院子的弟弟妹妹们都“哇”地哭起来,我的心也像被飞转的车轮辗轧着一般疼痛。我疯了似的跑进屯外的树林,抱着一棵大树放声痛哭。
随后,我赶紧去找姑父。姑父对我说:“你爹的事我管不了,我已经申请回避这个案子了。”为此,姑姑还跟姑父大闹一场。
父亲被抓走后,我们的生活更艰难了。我们兄妹9人,我是老大,家里没有一个壮劳力,但大人的活我们也得干。冬天到了,院子里的柴火开始空虚,又到了每年里摸起大耙杆儿的时候。大人搂柴火是在大耙杆上挂着耙连子,在甸子上到处走动,直到耙连子里面的柴火胀满。搂满一耙连子柴火得走一里多路,一天能搂30多连子柴火,累得筋疲力尽。我虽然才15岁,但长得膀大腰圆,能挂上耙连子搂柴火。大妹14岁,也跟着上甸子搂柴火。但女孩没多大劲儿,经常拉空大耙。二弟12岁,拿着小耙子搂柴火。我们哥儿仨干了10多天,总算搂够了烧柴。
与搂柴火相比,推碾子拉磨更难。当时我们屯还没有通上电,吃粮还得靠推碾子拉磨。我们家人口多,一个月就得磨一次米和面。我是老大,是干活的主力。玉米面好磨,碾米就不容易了,得讲技术,尤其是小米最难碾。谷溜子放粗了,谷皮儿碾不掉;谷溜子放细了,米被碾碎。风糠也需要技巧,风扇摇快了,米被吹进糠里;摇慢了,糠吹不出去。我们每次碾的米都是囫囵半片,吃起来咯吱咯吱直响。
我们兄弟5人,俗话说,“半个小子,吃穷老子”,我们哥儿几个虽然年龄不大,也都挺能吃。怕口粮不够吃,母亲很少给我们做干饭,多数时候是喝粥,且粥里总要放青菜,如白菜、萝卜缨子、甜菜缨子等。一次,母亲用草木耳(雨后地面生出的菌类生物) 加小米煮粥,二弟吃后中了毒,嘴不好使,流口水,送医院抢救才转危为安。
父亲被关起来,我们家成了“坏分子”家属,低人一等。母亲生小弟弟在月子里坐下病,手麻得厉害,向生产队借钱看病。那时社员手里都没钱,有事就向生产队借钱。队长赵××说:“没钱。”母亲说:“别人结婚几百块钱都借,我就借10元钱还没有吗?”赵××说:“有也不借,你家啥身份不知道啊?”母亲憋了一肚子气,含泪回到家。秋天分口粮,最后给我家分。我发现分剩下的玉米颗粒不饱满,就不愿意要。赵××说:“就这玩意儿,爱要不要!”我跟他理论了几句,没办法只好抱着瘪玉米回家。
 父亲被释放,磨难没有结束
父亲被释放,磨难没有结束父亲是拘留,按法律规定拘留不超过半个月。然而那个年代公、检、法处于瘫痪状态,已经无法可依,结果父亲被拘留了半年才释放回家。
即使这样,父亲所受的磨难仍没有结束,因为父亲是身上有“污点”的人。
1973年,我高中毕业回乡参加生产劳动。为了给我安一把锄头,父亲顶着烈日徒步去离家5里地的商店买了锄钩、锄板。锄杆商店里有,8角钱就能买到,但家里穷啊,11口之家全靠父亲一人挣工分养活,一年到头分不到钱还欠生产队一大笔债,8角钱在我们家也算不小的数额了。为了省下这8角钱,父亲在自家栽的树上砍了一根树杈做锄杆。第二天,我扛着一把新锄头到生产队上工了。
万万没想到,安这把锄头又给父亲招来祸端。晚上,队长赵××把我叫到队部问:“锄杆在哪儿砍的?”我说:“在自家园子里砍的。”队长又问:“是谁砍的?”我说:“是我爹砍的,不行吗?”队长阴沉着脸说:“不行,这是乱砍滥伐。”我争辩说:“自家栽的树怎么能算乱砍滥伐?再说又没砍大树,只砍了一根树杈。”队长见我和他争辩,急了,厉声说:“你们随便砍树还不老实,明天开批斗会,批斗你爹!”我的头“嗡”的一声,心想这下坏了,我爹又要遭殃了。
批斗父亲的会场设在生产队队部的院子里,父亲被押进会场,脖子上挂着“ 破坏国家财产坏分子”的牌子。批斗会开始,队长首先讲了批斗我父亲的原因和意义,然后要求大家批判发言。全场一片沉静,大约过了几分钟,一个愣头青小伙突然喊起了口号:“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誓死保卫国家财产……”
他一遍一遍地重复喊这几个口号,也许是天气炎热,也许是大家对这种批斗会司空见惯,没什么新鲜感了,所以尽管他卖力地喊口号,但跟着喊的人寥寥无几。人群中偶尔发出孩子们的嬉笑声,一些老人私底下也小声议论:“ 这点小事算啥啊,这么批斗人家有点过分吧?”见没人发言,队长开始审问我父亲:“你知罪吗?”父亲回答:“不知罪。”
队长又说:“ 你砍树是破坏国家财产,是犯法,你知道吗? ”父亲说:“那是我个人家的树,我只砍了一根树杈,不影响树的生长。”队长勃然大怒,将手重重地拍在桌子上:“你犯了法不认罪,还顶撞领导,你是不是还想进拘留所?”父亲一听这话,无所谓地说:“ 你愿咋地就咋地吧!”第二天,父亲又被送进公社学习班。
老实本分的父亲,竟然进了两次学习班、一次拘留所!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父亲进拘留所那次。记得父亲从拘留所回来时,很长时间彻夜不眠。他一袋接一袋地抽着旱烟,一阵阵地干咳,一句句地自言自语:“我就打他一巴掌,凭什么关我半年?”
许多无可挽回的悲剧,我们无法苛求任何人,只能怪自己失了手。这是命,也是运,因为命运都在我们自己手中。父亲的悲剧,虽然发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父亲的吸烟声、干咳声、自言自语声,像刀子一样扎着我的心。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这几种声音还完整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也扎了我几十年。我为自己所做的错事,必定得付出代价。不是物质上的,是精神上的,而精神这个无法直观目睹的东西,我又何等看重。所以,每当想起父亲所受的冤屈、所遭的罪,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
我的父亲,一个斗大字不识两口袋的普通农民,您蒙受了走向黄泉时都不能理解的冤枉。可是父亲啊,您知道吗?是您的儿子把您送进了拘留所!如果我当初不提供假材料,“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他们没有证据,也不至于把您抓起来关半年。老话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身为男子汉,什么都可以被夺掉,但这个“志”不能丢。都怪儿子无能,最终屈服于自己内心的软弱,可耻地丢了“志”。我没有做到表里如一,无所畏惧,悔得肠子都青了!
父亲,您在世时,我一直没有勇气对您说明, 让您始终蒙在鼓里,儿子是没脸直面您啊!人说世分阴阳,如果有地府,愿您的灵魂不散,待我将来到那边时把实情告诉您。我要向您说出在心中背了千万遍的忏悔:对不起,我可怜的父亲,请求您原谅我。
[责任编辑:杨晓晨 PQ038]
责任编辑:杨晓晨 PQ038
- 笑抽

- 泪奔

- 惊呆

- 无聊

- 气炸

网罗天下

凤凰时尚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