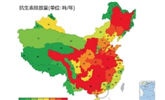蓝莓讲述:我愿用性命换回父亲
2016年12月28日 17:33
来源:凤凰时尚
作者:蓝莓
吴老师今年已经74岁,可每当想起他的爸爸,那种悔恨交加的心情竟让他喘不上气来。他悔恨、他羞愧,就连现在他都在想:爸爸出车祸的那一刻,如果能让他用生命去换回爸爸,他都毫不犹豫。

他悔恨、他羞愧,就连现在他都在想:爸爸出车祸的那一刻,如果能让他用生命去换回爸爸,他都毫不犹豫。


吴老师今年已经74岁,可每当想起他的爸爸,那种悔恨交加的心情竟让他喘不上气来。他悔恨、他羞愧,就连现在他都在想:爸爸出车祸的那一刻,如果能让他用生命去换回爸爸,他都毫不犹豫。
 我的童年
我的童年我上面有三个姐姐,我三姐的小名叫“换小子”。盼星星,盼月亮,1943年,我父母终于盼来了我。我的小名叫“连生”,父母是想接着再生男孩。听我妈妈说,我生下来全家都欣喜若狂,因为“二亩地里就一棵苗”,我二大爷有三个女儿也没男孩。可是,爸爸在我5岁时的一顿胖揍,让我刻骨铭心,使我觉得自己也没有那么金贵。
我被打的原因是这样的。一天,我正和同院的一帮小孩玩耍,突然尿急,便对着邻家的木障子尿了过去。恰好障子之间有一个小孔,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尿尿的技术很高,可以对着小孔尿出去。
我正在得意时,对面的那个媳妇像疯了一样大骂起来:“谁家的鳖羔子往我家大酱缸里撒尿!”之后她找到了我家,对我连推带搡,并骂道:“还知书达理的人家呢,养了一个这样的死孩崽子。”
爸爸这时拎了一个家伙,那是他平时最爱吹的黄铜做的箫,劈头盖脸地朝我打了过来。尽管我左躲右闪,可是腰、腿、屁股已重重地挨了几下。若不是有人挡着,打在头上我就惨了。
晚上快睡觉时,爸爸的恨意没消,因为我家的酱赔给了人家,就又从被窝里把我拎了出来。这次是用大擀面杖打的。现在想起当时的情景,和贾政暴打宝玉是多么的相似。我高烧三四天,夜里净说胡话,爸爸和妈妈也懊悔不已,破天荒地买了一包绿豆糕和一包槽子糕让我吃。可是我疼得要命,哪里吃得下?当我看见那擀面杖上还有一丝血迹时,心里恨我爸爸恨得牙根儿直痒。
等我疼痛减轻了许多时,我爸爸来看我,并用开水冲了三块绿豆糕让我吃。我就不吃,心里想:就不吃,让你后悔去吧!过了几天后,我哪还有那个志气,可想吃时早没了,都让我那个“馋猫”三姐吃光了。
就在我找绿豆糕时,无意中瞥见了爸爸打我的那支铜箫。我知道,它是爸爸的宝贝。我从小就听说我爷爷是满族人,会吹《苏武牧羊》,我爸爸也常吹这支曲子,尽管听起来很悲凉,可是真好听。可当时的我哪里还想悲不悲、好听不好听的,我的屁股已经全是紫黑色,出血水了,绿豆糕又没了,这都让我气不打一处来,我便将箫藏了起来。恰好有一天来了一个收破烂的,我便偷偷拿了出来,卖了5角钱。
事后我方知那是我太爷爷遗留下来的,箫上面还刻有字,现在想来,那也是个“文物”了。直到有一天我爸爸想吹箫时,才发现没了,咋找也找不着。可哪有不透风的墙,爸爸已经猜到是我干的。
也许爸爸出于内疚,没有追究这件事。半年多以后,我和同院的几个小孩捡破烂卖钱,我分到1角6分钱,给我爸爸买了一个竹子做的箫。尽管竹子的箫很精致,可那也比不上我偷卖的那个铜箫,那可是传家宝啊!但这竹子的箫也补偿了一点我对爸爸的亏欠心理。
我的小学是在长春东四道街小学读的。学校的对面是东二小学,就是以前的长春天主教堂。我小学一二年级时在两校的知名度非常高,因为有一次我在教堂里的两个学校学生演出时跳了一个舞蹈《马车舞》。我扮演一个小车老板,三个小女生穿着超短裙扮演三匹小马。演出服装很华丽,我扮演的车老板超萌,憨态惹人笑破肚皮。就是这个节目使我名声大噪,不仅参加了在长春市体育馆的全市各校代表演出,而且和苏联儿童联欢时也做了演出。那时的我长得小巧玲珑,说话细声细语,若只听声音,都会认为我是个小女孩。
那是在1951年的时候,在南湖的伪满时建的大楼里(后来称024部队大院),我代表长春的小学生慰劳抗美援朝伤病员演出时,出了大丑。那时已是晚上8点多了。我的《马车舞》是压轴节目,之前一个节目是小歌剧《献给志愿军的慰问袋》。就那个节目要结束时我尿急,想要尿尿,可带队的唐老师说,马上就要出场了,先憋一会儿。这时的我是强憋着尿跳完了这个只有4分多钟的《马车舞》。
我也是被尿憋的,这舞跳得超狂,志愿军伤员的掌声也狂响个不停。可结束时,我哪还有心情欣赏这掌声,我都忘记了应先敬个礼,没有从侧台退出,直接想从台上跳下来。是一位志愿军叔叔怕我从台上跳下摔坏,用双手抱住了我,还亲着我的脸。
天啊!这时的我,自己都不知尿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反正志愿军叔叔的前大襟已湿了一大片,我穿的彩裤还往下嘀嗒水呢!
因为天黑,唐老师雇了一辆马车把我送回了二马路的家。这时让我无地自容的是,我妈妈听说我尿裤子了,也不顾有唐老师在场,劈头盖脸地在我那光头上打个山响。唐老师拼命地拉着,可是那大嘴巴真是雨点般往下落,我的左脸立即肿了,嘴角也出了血。我狼狈地“哇哇”大哭起来。
这次暴打后我对我妈妈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妈,我是不是被抱养的?”妈妈以为小孩子开玩笑,刚要举手打我,我又说:“是不是咱家没小子,才把我从别人家要来的?”这时妈妈举起的手放了下来,骂道:“这是哪个遭天谴的人说的?”
那时我的脸肿了还没全消,妈妈把我抱在怀里,没有言语,可脸上却挂着泪水。她也许后悔打得太重了,可我的这句话像刀子一样刺痛了妈妈的心。
我不仅因为跳《马车舞》出名,更出名的是一跳舞准尿湿裤子。那是在中国俱乐部(后改为红星剧场)的一次汇演时,我扮演“除四害”中的一只苍蝇。演出结束时,我急忙跑到厕所。情急之中,我把原来的活扣儿裤子,一下拽成了死扣儿。结果裤子没解开,尿已经从裤腿流了出来。
又是唐老师把我送回了家。可这次妈妈没有打我,反而还向邻居夸奖我:“我家小连生子,名气大着呢,谁不知道?”可她从不向外人提我尿裤子的事。有位邻居大妈说:“听说你家孩子在台上演出时把裤子掉了?”我妈妈反倒打趣遮掩说:“小男孩掉个裤子怕啥?总比尿裤子强。”
多年以后,电视剧《年轮》播出,其中有一首插曲引我共鸣,让我感触颇深:“一条小巷里,住着我和你,一起去上学,一块去淘气……童年的歌是爸爸的巴掌打在屁股上,童年的梦是妈妈的眼泪流淌的希冀……”
 一封家书
一封家书现在的我,有时也像鲁迅小说中的祥林嫂一样,不论别人是否愿意听,总是自言自语:“我真傻,都成年了怎么啥都跟父母说?你自己苦、自己难,难道告诉父母就能减轻吗?”是啊,男子汉有泪应该往肚子里流,对父母诉说只能让他们心碎和担忧。
为什么我说自己傻?因为正是我的一封家信,才导致爸爸忧心忡忡,神不守舍,结果爸爸在一次上班的途中出了车祸。那一天是1976年1月21日,爸爸57岁。爸爸走时没留下一句话,因为肋骨扎在肺上引起了气胸,抢救无效。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从小能歌善舞、天真烂漫的我,压根儿没想到,自己成年后会活得这么复杂,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有时几乎让我绝望。这一切,皆因我爸爸出身地主,在解放前集体加入过国民党。也就是说,我受了他的牵连。
我是1967年的大学毕业生。因为“文革”,1968年下乡,在扶余县下属的一家国营农场中学当教师。
当初下乡时,我所在的那个农场同时分去了12个大学毕业生,除了医大、师大的干了本行,其余兽大、农大、农学院、工大的毕业生都下地干了庄稼活。当时提倡大学毕业生当农民,可是谁敢怀疑国家拿出那么多钱培养一个大学生,目的就是为了当农民呢?
我虽然家庭出身不好,但是爸爸在长春市教育局文教科上班,任副科长一职,所以我的出身一栏都是填写的“职员”。即使这样,分到农场后,我仍被视为隐瞒了家庭成分的人。在“文革”清队时,我虽是农场中学的教师,可在贫宣队的眼里,我则是地主的狗崽子、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到场部多次强烈要求更换我,说不放心把贫下中农的子女交给我。多亏当时有文件,师范类、医学类毕业可不参加劳动锻炼。
虽然我有幸分到了学校教学,可过了五六年后,跟我一起分去的大学毕业生基本都调回长春工作了,而我却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单位放别人也不放我。
当时的大学生很少,可谓天之骄子,毕业分到了艰苦的农村,感到一下子从天堂到了地狱,而且还抽不回来,这成了爸爸的一块心病。做为一个父亲,不能保护自己的孩子免受天灾人祸的侵扰,让爸爸十分内疚。爸爸在给我的信中多次提到:“都怨我,如果我出身好,我的孩子早回来了!”爸爸总是说:“艺民,你只要不怨恨我,我就满足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特别困难。生产队到冬天每家分一车烧柴,而我是教师,属于“臭老九”,地位与普通社员不能比,只给分半车。我又生活能力差,打不到柴火,家里冷得滴水成冰。
因为我家的柴火垛总是漏雨,一到晴天就得晒柴火。我爸爸知道后很是惦记,一到下雨天就担心我吃不上饭,竟让我妈妈给我邮一块能遮挡柴火垛的大塑料布……
我在农村结了婚。1975年,我妻子生第二个女儿时,爸爸给我们寄来了10元钱,还有一封信。我记得爸爸在信中安慰我说:“艺民啊,姑娘、小子都一样,我看还是姑娘贴心!”
我到农村以后,很少回长春的家。我不愿意回去是有原因的,主要是感到深深的自卑。那时弟妹们小,不懂事,看我穿得土里土气,总是对我一口一个“屯老二”地叫。有一次我回家,家里来了客人,吃饭时别人都上桌了,只有我还在厨房忙活。爸爸招呼我快上桌吃饭,一个弟弟却说:“别让屯老二上桌了。”这是我无意中听到的话,当时无地自容,眼泪往肚子里咽。那时,连我妈妈都会开玩笑地说我:“这屯老二……”
我因此不爱回家,也尽量避免回去。有一次我去长春办事,为了不想再遭到尴尬,自取其辱,我就花了10元钱,在长春火车站旁边的泰山旅社住了一宿。那是个破烂不堪的旅社,但即使这样,我也觉得比家里强。那一宿,我心中五味杂陈,泪湿枕巾,无法入眠。
我的境遇爸爸都看在眼里,也疼在心上。所以,他从不催我回家过年,他是为了维护我的自尊心。
爸爸是家中最理解我、最疼爱我的人,所以我写给爸爸的信最多,但基本上都是报喜不报忧。
那是1976年春节前,每逢佳节必思亲,我来农场8年了,还从没回家过过年,心中的思念和委屈一言难尽。于是,我给爸爸写了一封长信,向爸爸诉说了这些年来从未说过的遭遇。
那时虽是“文革”末期,但家庭成分还是困扰着我。在我的办公桌上,经常出现“打倒地主阶级”的粉笔字,令我心理压力很大。还有一件让我难以启齿的事,发生在“文革”初期。在一次全县的文艺调演中,我因擅长跳舞,在《洗衣歌》的舞蹈里扮演了一个解放军小战士。演出结束后,已经是晚上8点多钟了,我只好和演出的学生、贫宣队睡在了一起。就是在那个晚上,我受到了人生中的一次奇耻大辱。
一个转业兵出身的贫宣队长鼓动、教唆几个学生扒我的裤子取乐。被激怒的我,和他们进行了一场捍卫尊严的搏斗。当时的我真变成了一头怒吼的雄狮,丝毫看不出我平时是那么胆小柔弱、逆来顺受。我操起了一把二胡,和他们拼了。二胡打成了两截,音箱已经破损不堪。一只长笛也让在我自卫还击时打得粉碎。
搏斗中,没有什么胜负之分,因为我寡不敌众,可他们也没占什么便宜。贫宣队长扒我裤子的手让我用竹笛重重地挫了一下,见了血。他没敢告状,因为他没有那个脸。
这件事传到了农场党委,尽管他没受到什么处分,可还是在老师们的一片骂声中灰溜溜地离开了贫宣队。
我痛定思痛,含着泪水在信上向爸爸一股脑儿地诉说了这一切。
几天后,我没有收到爸爸的回信,而是收到了我三姐的回信。信中说,爸爸接到我的信后,自己背着家人,偷偷地到外屋抹眼泪,这情景恰巧被我三姐看到。三姐看到爸爸哭得那么伤心、悲凉,当时就问爸爸怎么了,爸爸说没什么。有好几次,三姐都看到爸爸边看信边流泪,可他说啥也不给三姐看。于是,三姐来信问我:“你都跟爸说什么了?爸咋哭那样呢?”
大约十多天之后,爸爸就出了车祸!
事后,妈妈也回忆起爸爸看完信时的情景。爸爸对妈妈说这件事时,眼圈红红的。爸爸说:“都是我造的孽啊,让孩子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吃了这么多的苦……”
三姐总是埋怨我,说我什么事都跟爸爸说,是我害死了爸爸。我无言以对,因为三姐说得对。
三姐的话犹如万箭穿心,让我悔恨交加啊!是我让爸爸心碎了。我的爸爸,一个有责任感的父亲,一个内心充满内疚的一家之长,在他的生命结束的前夕,占据他脑海的大事,是想自己孩子的屈辱,是想自己孩子的未来……我真傻,永远都不能原谅自己。在那个年代,爸爸自己就够难熬的了,我的遭遇无疑让爸爸雪上加霜。我给爸爸写信时满脸都是泪水,泪水滴在信纸上,我想爸爸一定看到了,也知道那泪是从我的心里流出的。可是我的心在流泪,爸爸的心在流血啊!我当时怎么就没想到呢?!
 无穷的悔恨
无穷的悔恨我在爸爸去世的第二天才赶回长春。爸爸是长春三十五中学校的会计,尽管出身不好,又加入过国民党,在“文革”中却没有受到冲击;并且在工宣队老白的倡议下,给爸爸开了一个像样的追悼会,追悼会上的悼词也都是赞美的话。这也是爸爸生前对我愧疚的一个原因,爸爸常说:“本来是因我而起,可我倒没受什么苦,而我的孩子咋受这么多苦呢?这些苦应该由我来受……”
爸爸,我对不起你,我不是一个好儿子。可是,我再自责也拉不回爸爸了,再自责也抹不平我给爸爸的心灵带来的伤痛。
处理完丧事后我坐火车要回农场,可我心中却压着一块大石头,而且越发沉重起来,突然想起了我入团时的情形。在我上大学时因为出身不好,入团申请书和思想汇报写得撂起来有一米多高,后来在下乡搞社教时才有幸入了团。那时全国都在“向雷锋同志学习”,为了入团,我自己拿了个剃头推子,每天到街头义务为孤寡老人理发,风雨不误,坚持了半年。当我戴着闪闪发亮的团徽想向爸爸炫耀一下时,爸爸却眼含泪水说:“是我连累了你,不然你早就入团了。”我不知是喜是忧,心情难以名状。而如今,我的那封信却连累了爸爸,甚至让爸爸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当时我手拎旅行袋经过二马路路口,到爸爸车祸的出事地点时,一股冲动让我失去了理智。爸爸!你生前我对不起你,现在我要跟你去了,我会在另一个世界陪伴你,做一个孝顺的儿子吧!我跪在了爸爸出事的那个地方,双手捂住了脸,泪水顺着指缝儿流了下来。我期望最好是同一路线的公交车把我送到爸爸身边。正在我的灵魂要飞向爸爸的一刹那,犹如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眼前出现了爸爸那慈祥的目光,那是一个没有内疚、没有自责的世界……
一声刺耳的汽车鸣笛将我从幻想中惊醒,我捂着脸的双手移开时,眼前是一片诧异的目光。人群中有人惊恐地叫道:“怎么了?撞伤了没有?”这时的我慌乱地推开人群,拎起了旅行袋,像一个刚刚被追赶的小偷冲出了围观的人群。
感谢那刺耳的汽车笛声,感谢那围观的人群,也感谢我的妈妈、我的爱人和孩子们,因为在那一刻我不能再做傻事了。
由此我想到了另一件让我刻骨铭心的事,也使我对爸爸的愧疚加深加重。
事情发生在“文革”中期,我的同组老师纪小新,他和我的年龄相仿,当时也是20多岁。在一次批斗他爸爸的会上,他和他哥哥陪斗。造反派让他哥哥用皮鞭抽打父亲,若不打便是没划清界限。他哥哥在威逼之下打了几鞭。可是这不能满足那些灵魂已经扭曲了的人的贪欲,非要狠狠地打。于是,又有人提出让纪小新老师也打。我正在惊恐不安时,只见纪老师将挂在脖子上的有20多斤重的拖拉机铁轮向上抬了抬,一头猛地向会场的一根柱子上撞了上去。顿时鲜血四溅,有几滴喷在了柱子上。可这时的他还有意识,第二次又拼尽全力撞了上去,最后昏倒在柱子前,场面令人唏嘘。那些想取乐的人也无心批斗,批斗会草草结束。可我心里对纪老师肃然起敬,扪心自问,如果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做出像纪老师那样的举动吗?我恐怕做不到,因为我缺少一个男子汉应有的担当。我写信跟爸爸诉苦,就说明了这一点。
 亡羊补牢
亡羊补牢爸爸带着对我的惦念和担忧离开了。如果说以往我还有理由抱怨生活给予我的磨难太多幸运太少,那么此后,我再不会那么矫情了。我在农场干了14年后,于1982年调到松原市,在油田的一所高中任教。在此后的30多年中,我发愤地工作着,我相信不管遇到什么艰难险阻,我都将微笑着独自面对。
在我的教学生涯里,我当了近20年的班主任,其中高三毕业班的班主任我干了近10年,并获得了全国数学竞赛一等奖的指导教师奖。退休后,我应聘到北京的一所“贵族”学校,并连续10年被评为先进教师、优秀班主任。当我在爸爸的墓前祭拜时,我声音哽咽,可内心却有一种自豪感;似乎爸爸就坐在我面前,我动情地说道:“爸,你的儿子已不再是一个穷光蛋……为你的儿子骄傲吧!”
我把已经不可能再给爸爸的爱尽情地献给了妈妈。欠爸爸的债今生都还不了,可对妈妈的债我绝不会再欠了。
我们兄弟姐妹共7人(我有两个姐姐在解放前饿死了),尽管在我刚起步时经济条件也只是一般,可是7个孩子中我是给妈妈汇钱最多的一个。每当妈妈过生日时,我都给老人家寄1000元,让她买蛋糕、鲜花。在妈妈腿脚不灵便时,我给邮2000元买轮椅。我明知用不了那么多,但我告诉妈妈,谁推她散步多,就给谁当小费了。在给爸妈买墓地和发送妈妈时,我一共花了6万多元,没有用弟妹们一分钱,可我心里高兴。
记得我在北京打工时,妈妈已经86岁了。听说我要回长春看她,本来是三姐接的电话,可是电话里却是妈妈的声音。她大声说:“你问问艺民,他想吃啥?”本来我是想问“妈,你想吃啥”,可是我顺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妈,我想吃你做的手擀面,要酸菜卤的!”
其实,我还想对妈妈说说爸爸。我想说:“我想爸了,爸还活着多好。爸还没去过北京呢,我真想像少数民族那样做一个竹子背篓,背着爸看看天安门……”

[责任编辑:杨晓晨 PQ038]
责任编辑:杨晓晨 PQ038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网罗天下

凤凰时尚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