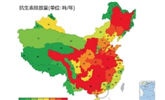蓝莓讲述: 提起父亲,我就想起那扎心的岁月
2018年05月29日 15:00:58
来源:凤凰网时尚
作者:蓝莓
小玉说,她老伴也不支持她写这个稿,他老伴说:“你这是何苦呢,写一段,哭一场,你还要不要眼睛了?”

“没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很难体会到我当时有多难,有多怕。”


小玉的稿件是手写稿。在稿件末尾,小玉给我留言:“蓝莓老师,如果能发表,请记住落款上写上‘小玉’这个名字。请不要把我的电话告诉任何人。拜托了!”
在发稿前,我约小玉就这篇稿件见面详谈,以便补充、核实一些内容。采访完毕,小玉已泪流满面。等她稍微平静一些,我问起为何如此留言。小玉说了一番令我震惊的话:“我现在还有顾忌,有些担心,怕有第二次“文革”,怕我现在说的这些将来再被人抓住把柄。
到时我可能两眼一闭,啥也不知道了,可我还有一个女儿,怕对我女儿再造成伤害。”
小玉说,她老伴也不支持她写这个稿,他老伴说:“你这是何苦呢,写一段,哭一场,你还要不要眼睛了?”
小玉的一番话,给我以震撼,同时有些心酸,也理解了在采访里小玉跟我多次说过的话:“没经历过那场浩劫的人很难体会到我当时有多难,有多怕。”
 我那既苦涩又欢乐的童年
我那既苦涩又欢乐的童年一九五一年的腊月初五,白茫茫的大雪下了两天两夜,天寒地冻的冷。我出生在长春市老菜市场(现在的平阳街)副食商品后面的一个日本人盖的灰色二层小楼里。我家住一楼,紧挨着大门洞,屋里又潮湿又冷。但是院子很大,很宽敞。院里有两口大铁锅,是用来炒花生、栗子的。还有一台手推车。那时爸爸妈妈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生活来源是我爸和爷爷一起做点小买卖。卖点水果之类的东西,每天出鲜货床子,挣点钱来维持生计。
爸妈共生了六个孩子,我上面有一个姐姐,我是老二。在我三岁时,得了“百日咳”,一声连一声的咳嗽,憋得小脸通红,小小的身体两头扣一头。我妈给我吃了药也不见好,病情一天比一天重。我妈急得够呛,就抱着我去大舅家串门。舅妈看我病成这样,赶忙到隔壁的一个常年患气管炎的老太太家要来两片药(事后才知道是叫“百喘朋”),说这药特别好使。我妈连忙给我灌了下去。大约过了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口吐白沫,两只小脚上下乱蹬,抽了!我妈吓坏了,挺着大肚子(当时母亲已怀着弟弟)抱着已经小脑袋往后背脖的我,三步并作两步地往家赶。
走到院门口,爷爷看见了,从我妈手里一把抢过我,大声喝道:“一个丫头片子,还治啥?死就死了,别糟蹋钱了……”一直脾气温顺的我妈急眼了,一把把爷爷推了个跟头,就势抢回我,紧紧地抱在怀里,一路小跑,直奔“双桥子”(现南关区医院)。奚大夫是远近闻名的儿科中医大夫,他在我身上扎了八九根银针,不一会儿我就止住了抽,小脸也一点点有了血色。又拿了几包灰色的药面,吃了几天后,百日咳终于好了。是我那慈祥的母亲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一九五八年国家有了“公私合营”的政策,因为我爸有文化,国高毕业,就顺理成章地进了单位上班,工作是采买员。单位在长白路上,每天我爸骑着自行车上班下班,在五八年家里能有一辆自行车的人家还很少。到了周日我爸休息,就左手牵着姐姐的手,右手拉着我的手,一起到人民公园去游玩(现在的儿童公园)。人民公园到处是苍松翠柏,景色宜人。在绿草如茵的草地上,我和姐姐欢快地跑呀,闹呀,弯腰捡几个松塔,装在兜里,留着回家玩,真好!看谁捡的松塔多,我和姐姐俩比赛。我爸手扶树干对我俩说:“孩子,这松柏树就是到了冬天也一样翠绿,像夏天一样挺拔又好看,不像别的树,一到冬天就枝叶枯黄了!你们长大了要像松树一样不怕严寒,不怕困难,要像松树一样,‘任他桃李争春暖,守我松柏耐岁寒’。”我那时还小,不懂这句话的意思,但这句话,我始终记在了心里。
一九六零年,正赶上三年自然灾害。我当时也就八九岁吧,每家每户都要用粮证买粮,而且粮食是定量的。我妈没有工作,每月只给二十七斤半粮。当时,每家的粮食都不够吃,我妈把一个苞米面窝头掰成两半,一半给我,一半给姐姐。那时每家都油水小,都非常能吃,每天都填不饱肚子……偏偏在这时,住在齐齐哈尔市的老姑和老姑父又来到我家串门,一住就是半个月,也不张罗走。本来我们一家人都吃不饱,又多了两个大人,那时的日子真是难熬啊!
那时的小学校都上半天课。中午放学回家,下午我和姐姐领着弟弟一起拿着铁丝做的长钩子,到宽广的斯大林大街的路两旁去够榆树钱(就是榆树上开的圆形的小花)。姐姐个子高,她用铁钩子勾,我和弟弟用手捋,再把榆树钱装在布兜里拿回家,我妈就把榆树钱掺在高粱米面里做成窝头给我们吃。后来捋榆树钱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姐弟三人又去捋榆树叶子,我妈蒸成窝头,我们吃得可香了。
有一天,趁着老姑两口子不在屋,我问我爸:“我老姑他们怎么还不走啊……”爸爸说:“孩子,你老姑他们家粮食也不够吃,要不然他们怎么能把两个孩子扔给老人,到咱们长春串门,也是实在没办法,你千万不要说赶走老姑的话。大家都有困难,咬咬牙就挺过去了。老姑是你的亲老姑,我是她哥哥,人活在世上要讲仁义,要懂亲情……”
一天,我爸下班后不知从哪里弄到半块半圆形的厚豆饼,就是现在喂马的豆粕子压成的。我妈用菜刀小心地一片片一块块地削下来,放在水盆里,用温水泡开和白菜帮子炖在一起,吃起来可真香!
 翻天覆地的“文革”,让我刻骨铭心
翻天覆地的“文革”,让我刻骨铭心流逝的岁月和尘封的往事像一本扎满草刺的书,我真的不愿翻起,真的不愿、不敢、不想……
记得大约是一九六六年,初二的课程还没念完,史无前例的“文革”爆发了,到处是粘贴的大字报、标语;到处传来广播喇叭的批判声,高昂的口号声震耳欲聋;如火如荼的“文革”之火,燃烧猛烈。我家也未能幸免,因为我爸年轻时国高毕业后就参加了国民党,做谍报工作。我爸被造反派揪出来,定为“历史反革命”,采买员的工作被剥夺了,每天劳动改造,扫单位大院,清理垃圾,打扫厕所……就连我爸当采买员的每个月31斤的口粮也被剥夺,变成27斤。
在我爸被隔离审查的那段时间,他们十多个造反派每天轮流吃饭,轮流休息。他们威风凛凛地坐在食堂的大桌子上,逼迫我爸跪在冰凉的水泥地上,一遍遍地交代问题。说一遍不行,两遍不彻底,三遍还有隐瞒。中午不让吃饭,到了晚上,他们还不放过我爸。他们用100度的大灯泡子挂在我爸的头顶烤着,整夜整夜不让睡觉,就是闭一会儿眼睛也要被踢几脚。吆五喝六地大声恐吓、谩骂,动不动就拳打脚踢,十多天不让我爸回家。
我妈和我们姐弟几人十分担心我爸,可又不敢上单位去找,心里实在着急。就在我爸离家的第十二天早上,终于被他们放了回来。看见我爸用淌着血的手推开了院门,一头浓密的头发被剃得精光;眼皮浮肿,消瘦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苍白得吓人;上班时穿的整齐的衣裤被打得又脏又破。看见我爸摇摇晃晃的身躯随时就要倒下……我们姐弟一拥而上抱着我爸颤抖的身体,放声大哭!
当我和姐姐拿来了棉签,又从抽屉里找出“二百二”(红药水),轻轻地给我爸上药时,发现我爸脖子上的一道血印子很深,那是被批斗时那些丧尽天良的造反派把挂着8号线的粗铁丝系在我爸的脖子上,铁丝已深深地勒进了肉里。正赶上是夏天,天气热,人每天都出汗,那一定是钻心的疼。上着二百二,我和姐姐又哭成了一团。人谁不是父母所生,谁不是血肉之躯,谁能受得了这样的折磨?我爸紧闭着双眼,用颤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顶,轻轻说:“爸没事,别哭了……”看见我爸被折磨成这样,我心在流血,这种撕心裂肺的疼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文革”结束后,我还是常常被噩梦惊醒,梦见我爸那血肉模糊的右手,和那苍白的脸颊……
在我爸在单位挨批斗时,我家里也不消停,街道上的造反派和委主任一伙把我家的院墙上、木栅栏上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上写着:“打到历史发革命分子XXX!”我爸的名字被红色的毛笔打上两个粗粗的大叉!十分难看又刺眼。
一天下午,十几个穿着黄军装的造反派凶神恶煞地踢开了院门,手里拿着大棒子像土匪一样抄了我的家……他们踢倒了桌椅板凳,把柜里的衣裳翻得乱七八糟,胡乱地扔在地上。我妈连忙用身体护住我两个小妹妹。奶奶在去世前留给我妈的两个金戒指和一个手镯都被抢走了,大约有20多本用黄表纸印的书也被烧成了灰烬……这还不算完,造反派又逼我妈交出手枪,我妈说我家没有枪,他们不信,连装着菜和萝卜的菜窖都被翻了个底朝天……我们几个孩子整天躲在家里不敢出门,家里没有盐了,姐姐一路小跑去买,仍然躲不过邻居半大孩子扔过来的石头子,还高喊着“打死黑帮狗崽子”……

人的一生都要尝过苦辣酸甜,这才是完美的人生,然而揭开心灵的伤疤,是那样痛彻骨髓……
姐姐是八中的学生,下乡到通榆县乌兰花公社。1968年12月,我随学校安排下乡到本市郊区的西新公社,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来到这个叫小凉山的屯子。我们集体户共12个学生,6个男生,6个女生。刚下乡时对什么都感到新鲜,从来没有看见过社员家放在火炕上的火盆,从来没有看见过用辘轳摇的大水井。然而,这一切的新鲜都被繁重的体力活压倒了。
夏天,天还没亮就跟着社员一起扛着锄头去铲地。小小的高粱苗长得不到一窄宽就要开苗了,我学着社员的样子左一棵右一棵地挥舞着锄头,把密密的多余的高粱苗铲掉,留下健壮的苗。留苗要成拐字形,以利于通风。一条垄没有铲到三分之一腰就累得酸疼酸疼的,握着锄扛的手指好像僵硬了似的不听使唤。收工回到集体户,扔下锄头,一头躺在炕上,浑身像散了架子似的,饭都不想吃。往墙上一瞅,满墙是绿色的火苗,连眼睛都看花了。
我们生产队的队长和会计不知道什么时候偷偷去了市里到我们集体户学生的家长单位取外调,回来后,社员都议论纷纷,都知道我家有历史问题。我们户还有一个女同学家里也有问题,于是有几个不懂事的半拉子(就是年龄小,挣半个公分的半大小子)在干活时欺负我俩。在春天撒粪时,我们女生每人挑着两个竹筐,半拉子用铁锹把粪土撮进竹筐里,我们挑到地里,隔不远倒一堆。轮到我刚把竹筐放下,一个叫红脸子一个叫白脸子的半拉子就猛撮土装满了竹筐再用铁锹拍实成了。给别人都是轻飘的装满就行,可对我俩是拍了又拍。
我左右手把着扁担沟子,沉甸甸的粪土压得我难以直腰……一天下来,肩膀又红又肿,火辣辣的疼痛。干了两天后,我户那个家有问题的女同学就回家了,我仍然咬紧牙关坚持出工……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几年过去了,我们户12个同学大都回了城上了班。好心的社员王叔,看我每天干活累得够呛,又知道我家里是有问题不是根红苗正,很难抽回市里,就给我介绍了对象,是本屯一个勤劳善良的小伙子。这一年在五月节的前两天,我户同学都回了家,只剩下我和另一个家有问题的女生留下看户。晚上我户一个男生来到我家串门,我爸问:“怎么小玉没回来呀?”“她还回来啥啊?有对象了,被对象家留下过五月节了……”我爸一听急了,第二天一早背着十斤大米,买了二斤切糕,坐着汽车,又步行十八里地来到集体户。又领我到小伙子家串门,见过他家父母说:“我家小玉年龄小,也不懂事,我坚决不允许她这小小的年纪就搞对象……”当天,我爸就把我领回了家,并且严肃地跟我谈话,告诉我累了就回家住几天。由此,我爸严格地规定我家六个孩子谁也不许在26岁以前结婚。
春去秋来,星移斗转,最后我们户12个同学只剩下我一个人,每天和大黄狗相伴,挺着这空荡荡的三间房。
在集体户干活累了,我就回家住几天。一天吃晚饭时,我妈擀了面条,又卧了两个鸡蛋,端给我吃。因为那时我已有了胃病,总吐酸水,烧心。我爸说:“小玉,快点吃吧,苗条软乎”……可是,我刚刚吃了几口,胃就丝丝拉拉地疼。我放下饭碗,手捂在胸口,双眉紧锁。“咋的了,胃又疼了,”我爸问道,“小玉,爸给你找药,你等着……”“找什么找?我不用你找!我疼死算了,疼死省心!别人家的爸妈都是贫下中农,为啥咱家不是?爸!你年轻时干点啥不好,偏要去当国民党,你害死我了!摊上你这样的爸,我真倒霉!看见我的同学一个个都抽回来了,就我二次政审都不合格,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死了算了……”我越说越来气,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被我狠狠地摔在地上。然后,我掀开棉被,盖住脑袋,大声地哭起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真是大逆不道,禽兽不如,说出这样的话,无疑是在爸的伤口上撒盐,多伤爸的心!谁在娘胎里就能选择出身?别说是普通人,就是神仙也无法选择出身,这是亘古不变的事实。
1974年秋天,西新公社五七连的干部开始组织并户,我被从西小凉山并户到了三里外的双龙大队。这个户的成员都是几个集体户抽剩下的人,还有七一届、七二届的毕业生。在新集体户里,我又坚持了两年。在1976年的12月,我终于被西新公社直接戴帽给双龙大队一个“可教育好子女”名额抽回了长春市。苦尽甘来,结束了长达8年的知青长跑,回到了盼望已久的家。

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录取通知书时,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伤心的泪水,放声大哭。因为,我再也看不到我亲爱的爸爸了。
想起那疼爱我的爸爸,他再也不能和女儿分享这骨肉团圆的天伦之乐了,他再也看不见女儿那欢快的笑脸了。我的眼在流泪,我的心在滴血……
我爸去世了,也就是在我抽调回城的两个月之前!1976年10月份,各家各户都在买冬储菜。我爸在单位上班时,单位也给员工分土豆。这个扛土豆的任务我爸自然少不了。当我爸扛着满满的一袋土豆时,一不小心,土豆袋子从肩头上滑落下来,砸在了右腿的膝盖上,当时就红肿起来。回家后,我妈给敷上了“金黄散”,又给吃了“七厘散”。到了晚上十点钟,我爸就发起了烧,一看体温计40度。我妈连忙找出“安乃近”让我爸吃下。可高烧还是不退,脸颊烧得通红,盖上两双棉被还说冷。我妈一看不行,赶忙敲开邻居老朱家的门,借来了手推车,和弟弟一起把我爸推到了平治街上的二院。医生马上给挂上了吊瓶。
第二天一早,还不到7点钟,当我妈把买来的牛奶和馒头端回病房时,我爸就已经奄奄一息了,吓得我妈高声喊着我爸的名字,一边忙叫弟弟找大夫。可是,一切都晚了,我那慈爱的爸爸再也听不到亲人的呼唤了。他微张着嘴,好像有话要说,可是他已经说不出来了,永远地闭上了双眼。爸爸的死亡原因,医生诊断是“急性败血症”。
当我从集体户赶回家时,家里到处是一片哭声。看着墙上爸爸的照片,我哭喊着:“爸!‘文革’那样的批斗,你都挺过来了,现在这么点小伤你怎么就挺不住了呢?”
弟弟给我爸单位打了电话,单位来了两个领导,对我妈说:“他是黑五类分子,是专政对象,不能留骨灰,不能造成负面影响。”我妈要给齐齐哈尔市的老姑发电报,再给呼兰的王叔发电报,领导都不允许,说只能通知住在长春市的亲戚,让丧事快办。
在我爸出殡的那天,老叔不让我去朝阳沟,让我留在家里,陪伴我那哭昏过两次的妈妈。那一年,我爸年仅54岁。我这个不孝的孩子,连我爸最后一眼都没见着……更别说向他道歉,我悔恨终生。
2006年5月,我妈也去世了。我们姐弟俩在朝阳沟的南华苑买了一块墓地,立了石碑,把我妈的骨灰和我爸合葬在一起。因为我爸没留骨灰,只好把我爸的骨灰盒里放上一张照片。每年的清明节和春节,我们姐弟都会去扫墓,缅怀我们的爸妈。
远在天堂的爸妈,你们是否会原谅你们那不懂事的女儿!


[责任编辑:闻捷 PQ011]
责任编辑:闻捷 PQ011
- 好文

- 钦佩

- 喜欢

- 泪奔

- 可爱

- 思考

网罗天下

凤凰网时尚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