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莓讲述:“文革”时 我做过一件最值得炫耀的事
2014年08月07日 10:28
来源:凤凰网时尚
作者:蓝莓
/*2012.01.30b小情大事*/,#artical_real{padding-left:0px; padding-top:0; margin-top:-3px; clear:both;},#ar

蓝莓讲述:“文革”时
我做了值得炫耀的事
有一天,吉林市的读者蔡景余伯伯给我打来热线电话,他说:“我今年70岁,虽然大伙儿说这叫夕阳红,但我认为不要自欺欺人,这叫日暮途穷,比较实在,该做的事抓紧做完,少留点遗憾为妙。”
[本期关键词:师生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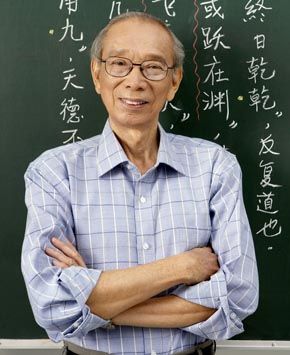

蔡伯伯是想为我主持的一个栏目《扪心》投稿的。《扪心》是一个以忏悔为内容的栏目,稿件上版的前提是作者曾经做了对不起人的事,且给人家造成伤害,从而引发良心的不安……
蔡伯伯说,他想对他的老师们忏悔。他对所有教过他的老师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从小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乖孩子,凡教过他的老师都喜欢他,把他当成宠儿。但他曾做过对不起老师的事。
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农村孩子,家在永吉县江密峰乡的一个小屯,家庭成分是富农,受人另眼看待。但他没有辜负老师们的期望,经过小学、初中各阶段老师的悉心培养,他没走任何门子,以优异成绩考上了省级中专——吉林省农业机械学校,学制5年。
蔡伯伯说,他“对不起”老师的事只要有两件。他先跟我说了他小学时“对不起”老师的事。
事情缘于“一瓶酒”。1958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春季里支援农业插秧。那一天我们插秧刚干了一会儿,突然一阵大雨把我们拍了回来。那年月没有塑料布之类的雨具,雨天上学披个蓑衣披个麻袋就不错了。老师和三十几名学生光着脚从二里地以外的水田地跑回教室,都成了水鸭子,穿的单衣都贴在了身上,直滴答水。
许多学生都小脸发白,上牙敲下牙。老师心疼得不得了,跑到供销社买了一瓶白酒,打开盖让我们喝,说是驱驱寒、暖暖身子,别坐下病。老师让了一圈儿,我们麻木地你瞅瞅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喝。老师气极了,一仰脖咚咚把酒喝了半瓶,剩下的连酒带瓶在空中划了一道弧线后啪地摔到地下,把门一摔扬长而去。同学们都傻眼了,收拾书包回家了。
后来我才缓过劲儿来,这瓶酒是老师自掏腰包买来的,是对学生的一片热心,是慈父般的爱。当时我是学习委员,大小是个头儿,我要是带个头,抿一口酒,同学们也都会照办的,这样既暖了我们的身子,又暖了老师的心,那将是多么和谐的结局。相反,我和同学们冷了老师的心,驳了老师的面子,把老师气个倒仰。我这个小书呆子,长着个木头疙瘩脑袋,光知道学生守则中“不抽烟不喝酒”的条款,却伤了老师的心。
我说,这件事虽然让老师伤心了,但可以原谅,不用忏悔也行。蔡伯伯就又给我讲了一件他初中时更“对不起”老师的事。
事情缘于“一罐咸菜”。1960年,我上初中,学校距我家十里地,走读,中午需要带饭。我带的菜是一罐芝麻酱拌咸菜丁。我把它放在教室的窗台上,省得每天拎着它。学校的教导主任是个脸色苍白体型胖胖的人。我逐渐发现一个反常的现象,这个主任每次巡察我们的自习情况时,总是拿起我的咸菜罐贪婪地闻了又闻,久久不肯放下,不下四五次之多,完全没有了师道尊严。
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我不应该把这个罐子放在窗台上?我莫明其妙,整不明白。后来在高年级同学给他献血,几番抢救无效死亡后我才知道,他患的是严重的胃溃疡,由营养不良引发的病。在那吃糠咽菜的困难年代,人们吃的东西没油水,都馋啊!更何况是一个营养奇缺的胃溃疡患者呢?那少见的芝麻酱香味诱惑着他,吸引着他……唉!我当时怎么没想到呢?都说有老年痴呆,我这个小痴呆也够呛了。我要是偷偷地问一句:“老师,你想吃这个咸菜吗?拿去吧,我家还有一坛子呢,吃完再拿。”那该多好!就是这样一件给濒危的老师一罐咸菜的小事我都没做,不是抠门,而是愚蠢,每次想起都追悔莫及。
我说,这件事确实挺让人后悔,但还是可以原谅,老师也没有怪罪你,你不必自责了。蔡伯伯叹了口气。他说:“那我就不说忏悔的事了,我最后给你讲一件我在中专时期最对得起老师,也是我一生中最值得炫耀的事吧!”蔡伯伯给这件事起了一个名字,叫“一条路”。
我是1963年上的中专,1967年——中专毕业的前一年,正好赶上了那个让人诅咒的十年动乱,耽误了毕业分配。虽然个人遭点损失,但比起那些开国元勋、大知识分子的遭遇和损失,又算什么?我也非常感谢这场运动给我上了一大课,一是让我看清了在非常时期一些人的丑恶本质和真实嘴脸,二是教会我怎样在没有路的地方闯出一条路来。
这得先介绍一下我们省农机校在“文革”前的简况。学校位于现在的公主岭市,设置机械和财会两个专业,学生毕业分配去向是各市县拖拉机站,职务将是机务干部和财务干部。
教师的水平是一流的。他们念大学时不敢报国家重点军工一类的大学,因为他们出身背景复杂,过不了政审那一关。他们有自知之明,忍痛割爱只好报农机系统的大学和专业,好在当时是“大办农业”的时代。我校教师中有费孝通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社会活动家,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的女儿女婿,有余瑞璜(中国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中科院首批院士,江西宜黄人。1952年,余瑞璜根据国家要在东北建立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的需要,来到长春筹建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物理系,亲自参加创建了中国第一个金属物理专业)的儿子,还有出身资本家等各种复杂背景的人。虽然他们的出身杂七杂八,却也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教各个专业和科目都是不含糊的,都是高手、硬手。他们都是忠心耿耿,立志报效祖国,要为农业机械化事业培育合格的机务和财会人才的。可是,他们在“文革”中不可抗拒地遭到了迫害。
在我中专毕业的前一年,摊上了那场全党全军全民共同的大灾难——“文革”。转眼之间一切秩序全乱套了,从中央到地方,打倒各级走资派的疯狂喊叫声不绝于耳,侮辱丑化走资派的大字报、“百丑图”触目惊心。学生们串联回来学了各地的“高招”,学了就用,不计后果,似乎明天早上就会实现“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了。
他们气势汹汹,不可一世,对学校书记、校长、中层干部等“黑帮”(“黑帮”一词主要指走资派,有时也泛指所有被打倒的“牛鬼蛇神”)老师们收集资料——就是档案中明明写着的东西,罗织“罪名”。“黑帮”老师们被他们剃鬼头、戴高帽、挂牌子。他们用皮带钢丝鞭触及“黑帮”老师们的皮肉,用丑化侮辱触及“黑帮”老师们的灵魂。谁敢反抗,谁敢逃避,连死都不敢想,那叫“畏罪自杀,自绝于人民”。呜呼,那时候上哪儿说理去!
1967年,是派性兴风作浪的一年。我们学校分成了两派,而两派的背后还都有军队表态支持。势不两立的两派之间的摩擦最后升级到武斗。我们这派人数少,而且对“黑帮”老师们比较温和,主张文斗。而另一派则不然,用武力说话,矛头不仅指向“黑帮”老师们,还指向了我们。我们这派的同学们连去食堂吃饭都要遭到追打。我也是挨打的一员。
1967年5月左右,远处传来了武斗的枪声,“黑帮”老师们担惊受怕,我们这派的学生也提心吊胆,不敢在这校再待下去了。怎么办?出路在何方?于是我向我们派的头头献上一计: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们几个不出名的小跟班带上比较信任我们的书记、校长、中层干部去一个势力强大的、与我们同一派的学校躲起来,让他们互相揭批,然后将揭批材料不时捎回学校,再由留校的同学油印成小报张贴出去。这样,我们既抓了“大方向”,又可以保护“黑帮”老师们和我们自己。头头采纳了我的这个建议。
于是,我们开始悄悄地行动,通知书记、校长和几个核心的中层干部准备钱、粮票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定于某日出走。
这些老师信任我们,欣然受命。于是在一天凌晨,我和王尔飞同学两人带领这帮“牛鬼蛇神”——网中之鱼、惊弓之鸟登上了去长春的火车,终于逃之夭夭了。
当另一派发现“黑帮”老师们集体失踪后,大为恼火,可惜慢了半拍。他们马上到这些老师家里撕下他们的照片(有的还是全家福中带着儿子耳朵的照片),到照相像翻洗后,再贴到“通缉令”上。他们非要抓回这伙“走资派”不可,略过不表。
话说我们投奔的目标,是吉林农大。同一派的战友格外亲,他们很欢迎我们。然而到了晚上,他们让我们帮忙往学校楼顶上运石灰、砖头、喷粉器、镐把等东西,说是战备,防止对立派的进攻。他们还要求我们派人参加值班站岗。
让“黑帮”老师们参加防卫,终究不是个事。第二天我们又转移到郊区兴隆山农机校。这个学校也是一面倒向我们这一派的,没有武斗的后顾之忧,学校的党政财文包括食堂的大权全部掌握在学生手中,我们可以放心地搞揭批了。
在揭批会上,书记、校长大概是被前段的轮番批斗搞糊涂了、吓蒙了,他们总想洗清那些人给他们定下的罪名,互相推托,想办法狡辩。幸好有勇有谋有心计的教务科长、党委委员翟延廷老师早有准备,他带了几年的党委会记录本,涉及到谁的问题,马上找到当时的会议记录。学校做的某项改革,依照的是什么文件,甚至连会上书记坐在哪儿、怎么说的,校长坐在哪儿、如何讲的,都一一记录在案。白纸黑字,不能更改,结果让书记、校长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翟科长说:他们让你们当“走资派”也活该,你们自己心里都不明白自己是不是“走资派”,还胡掐乱咬,还要把我们拐带上“白专分子”、“黑爪牙”等等。你们就不能挺起胸膛,据理力争?
我真佩服这位把教学和各项工作治理得井井有条,成果斐然的老师。他在这次批斗会上的表现,显然让他成为了批斗会的主角,使我对他的钦佩又升了一格。我们带领他们以摆事实讲道理的办法揭来批去,最后事实越来越清楚,闹了半天,他们的那些“罪名”是有些居心叵测的人在背后指使,或亲自指挥那些涉世不深的学生们捏造的。
书记、校长表态说,我们从入党宣誓那天起对党就没有过二心,谁也没有想离经叛道单跟党中央之外的哪个司令部走别的路线,“走资派”等罪名是造反派强加给我们的。我们就是真的被打成了“走资派”,也得保留申诉的权利。就这样,“黑帮”老师们和我们这些“红卫兵”小将的距离拉近了,几乎到了同一战壕的程度。
心理的压力减轻后,老师们自始至终一没挨打,二没受气,我们还组织他们帮助学校农场铲铲地、促促生产。在生活上,他们还可以在学校食堂花一毛六买一碗红烧肉改善生活。后来由于怕待在一处时间长了容易暴露,我们又搬到别的学校。
这期间,我们把揭批会的进展、材料、战果、花絮等写成材料,捎回学校,油印成小报散发张贴。因为“文革”还未结束,我们这样做,一是对“通缉令”的回应,二是让老师们的家属放心、让对立派死心。
几个月危险期度过后,大联合、三结合和复课闹革命的形势到来了,我们这伙失踪的人又悄悄地回到学校,且一个个精神焕发,安然无恙。我们当然不能张扬,还得夹着尾巴做人,因为“文革”没有结束,我们仍是“地下工作者”,不敢透露半点风声。
现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是我们在走投无路的形势下被逼出来的。尽管这条路充满了荆棘和危险,但我们还是在围追堵截中逃了出来。走是对的,使无路变成了有路,而且是唯一正确的路。我想,我们对老师们做了一件大好事。这样的事,网上罕见,报纸未闻。哪个敢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领着“走资派”们东躲西藏?你吃了熊心豹子胆吗?你不怕通缉吗?你不怕叫对立派侦察出来把你们连窝端吗?哈哈,我们胜利了。
蔡伯伯说,这段经历他以前不说,是迫于当时和以后的一段时期大环境不利,现在没问题了,这正合了《三言二拍》中的那句话:“雪隐白鹭飞始见,柳藏黄莺语方知。”
[责任编辑:范文婷]
29岁小伙恋上62岁老太 称做梦都梦到她
04/13 08:36
04/13 08:36
04/13 08:38
04/13 08:37
04/13 08:37
网罗天下
频道推荐
智能推荐

凤凰时尚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