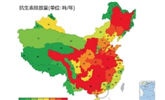埃博拉后遗症阴影再临:幸存者并未开启全新生活
2016年07月31日 08:52
来源:中国新闻网
在经历死亡率极高的埃博拉病毒折磨后,幸存者并没有真正开启全新的生活,大脑认知功能障碍、失忆、关节疼、肌肉疼,仍在摧残他们。
C 病毒的藏身处
对于很多埃博拉幸存者的眼疾,专家表示,这也是机体对病毒进行免疫应答的结果。更糟糕的是,即使在血液中被清除很久后,病毒还能在眼睛内复制。眼球为病毒提供了安全的庇护所,使它能躲避免疫系统的干预。研究人员曾发现,有一位幸存者的眼球里充满了埃博拉病毒。2014年9月,在塞拉利昂工作的美国医生伊恩·克洛泽感染了埃博拉病毒。他从一家美国医院出院后不到两个月,就觉得左眼十分疼痛,眼睛的颜色也从蓝色变成了绿色。当医生将一根针插入克洛泽的眼睛时,他们发现,眼球中的病毒数量比几周前血液中的还要多,而当时他已濒临死亡。
眼球并不是埃博拉唯一的藏身之处。睾丸、中枢神经系统和关节软骨也能成为包括HIV在内的多种病原体的庇护所。当免疫系统向外来入侵物开战时,身体有些关键结构可能会被免疫反应误伤。为了保护自己免受炎症侵袭,它们会采取抑制免疫的行为(释放免疫抑制分子或者制造物理屏障)。这些措施成了病毒的保护伞。
如果睾丸为埃博拉提供了庇护所,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些幸存者在症状消失后,还能在精液中检出病毒,并且还能持续好几个月。在西非疫情开始暴发时,世界卫生组织就警告人们,在埃博拉病毒血液检查呈阴性后,至少还要留意3个月,期间只能进行有保护的性行为。这个建议源自1995年刚果疫情中的一个案例,当时幸存者距离首次出现症状已经有82天,医务人员还是在他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
西非疫情期间,埃博拉病毒在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存活的时间变得更长了,可持续到急性感染后1年左右。在波士顿的会议上,法拉赫强调了这种现象,还报告了他们在利比里亚的发现。在急性感染18个月后,他们仍在幸存者的精液中发现了病毒。还有一些情况更麻烦,虽然病毒从一些幸存者的精液中消失了,但在随后的1年中,又出现了。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男性埃博拉幸存者需要在感染后1年内都实行安全的性行为,而且他们还需要定期复查精液里病毒的情况。
在蒙罗维亚的办公室中,法拉赫还有一份女性患者的档案,她的儿子在2015年11月死于埃博拉。报告显示,这家人没有与埃博拉病人或幸存者接触的任何记录,但是法拉赫相信,情况并没有这么简单。他认为,这位母亲可能与一位埃博拉幸存者发生了性关系,而她没有意识到埃博拉病毒是她在感染后传给儿子的。
法拉赫此前研究过一个案例,这个例子最有可能表明疾病是通过性交传播的。2015年3月,有一名女性死于埃博拉感染,研究人员发现,她曾与6个月前从埃博拉治疗点走出去的一位男性发生过性关系。这名男子的血液检查呈阴性,但是在精液样本中仍然检测到了埃博拉病毒。
D 绝望和无助
在约瑟芬离开位于蒙罗维亚的埃博拉治疗点后,她就在丝茅勒塔斯村的家中生活。那天午夜,她突然惊醒,让她醒来的不是噩梦或者头痛,而是腹部的阵痛。她爬起来去卫生间。可是,当她擦拭身体的时候,却看见纸巾上全是血。接着她的羊水就破了。“奥菲莉娅!”她叫唤着姐姐的名字。她们打电话想叫救护车,但是没有救护车能出车。她们给蒙罗维亚的一个无线电台打求助电话,却依然没有人来。
约瑟芬在卧室里来回踱步,在感到腹部像是快被撕裂开时,她会停下来用手撑墙站着。到了早上5点,她裹上一条栗色的拉帕(lapa,利比里亚一种传统的围裙样的织物)摇摇晃晃地走出了房间。如果没人上门来帮她,她只能到街上去寻求帮助。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整个村子都还在睡梦中。随着她大声叫喊,村里的妇女们纷纷走出房间。“帮帮我,请帮帮我,”她哭着喊道。但是没人愿意靠近她,人们都害怕接触这个几天前才从埃博拉治疗点出来的女人。当她走到土路拐角处的房子时,就再也走不动了。她倒在地上,背靠着墙,感觉婴儿就要从两腿间生出来了。
有5位妇女解下拉帕,朝约瑟芬走来。她们在约瑟芬周围围成一个半圆,好让围观的男性看不到她生孩子的过程。约瑟芬一边用力一边嘶喊着。“奇迹”诞生了,是个胖乎乎的小男孩。但是当她想把这个安静的孩子抱在怀中时,却发现“奇迹”并没有呼吸。
没人接近约瑟芬。这些女人看着她摇晃着她的孩子,呜咽着将孩子抱在胸前。只有她的兄弟走到身边,将“奇迹”从她怀里抱走,用一条黄色毛巾把婴儿和胎盘裹了起来,准备埋掉。
约瑟芬的母亲生前是一名助产士,也死于埃博拉感染。“为什么她现在不在这儿帮我?”约瑟芬十分痛心。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人们的问题随之而至:是埃博拉杀死了“奇迹”,还是没有人帮助约瑟芬导致“奇迹”未能顺利活下来?如果救护车来了的话这个孩子能活下来吗?病毒是否还潜伏在她体内,这些潜伏的病毒会危害她将来的胎儿吗?
约瑟芬也参与了幸存者研究,在拜访肯尼迪医疗中心时,她也向法拉赫提出了同样的问题。那天下午,她身穿一件露肩的豹纹衬衫,戴着搭配适宜的头巾,坐在法拉赫的办公室里等他答复。
法拉赫担心子宫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另一个庇护所,病毒躲在这里的同时,仍会影响幸存者的身体。也许庇护所里的病毒会再次扩散,甚至感染其他人。此外,他也在思索,约瑟芬身为埃博拉的幸存者而背负的压力,是否导致了她在被众人围观,又无人提供帮助的情况下,当街产下死胎。法拉赫考虑到:“当你不能再到市场上卖肥皂,当你得把钱包在纸巾里才能买菜,当你的男朋友因为你是埃博拉幸存者而不再爱你时,这一切会对你的身体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当这种影响施加给一个未出生的孩子时,又会怎么样?”
这就是他在思考的问题,可当约瑟芬问他时,他只能说:“我不知道,约瑟芬。我们正在试图找出答案。” 作者:撰文西玛·雅斯敏翻译郭晓
[责任编辑:李旭 PQ029]
责任编辑:李旭 PQ029
- 笑抽

- 泪奔

- 惊呆

- 无聊

- 气炸

网罗天下

凤凰健康官方微信
视频
-

李咏珍贵私人照曝光:24岁结婚照甜蜜青涩
播放数:145391
-

金庸去世享年94岁,三版“小龙女”李若彤刘亦菲陈妍希悼念
播放数:3277
-

章泽天棒球写真旧照曝光 穿清华校服肤白貌美嫩出水
播放数:143449
-

老年痴呆男子走失10天 在离家1公里工地与工人同住
播放数:1651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