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女性运动的詹姆斯·邦德”

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保加利亚裔法国人,巴黎第七大学语言学教授,心理分析学家,女性主义理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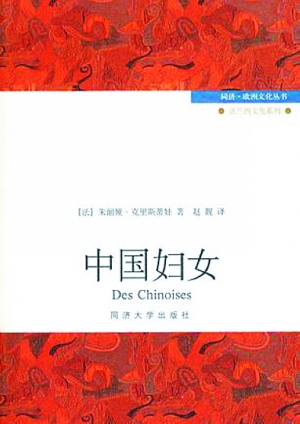
“我是克里斯蒂娃,在我身上大部分是女性特质,但我也有男性特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组成了克里斯蒂娃的性别。
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从传统中来的女性主义者,但我知道怎么去利用现代手段做女性运动,比如媒体。所以,我是女性运动的詹姆斯·邦德。”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这是2009年以来,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第三次来中国,这次她终于以学者身份来到上海进行一段比较长时间的讲学。在本周,克里斯蒂娃受“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项目的邀请,将在复旦大学做四堂专题讲演,四堂讲演的内容和她的精神分析理论有关。而克里斯蒂娃的另一个重要身份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家,她被认为是西蒙·德·波伏娃的继承者,“女性主义”或者说女权运动依然是她最为关心的议题。昨天克里斯蒂娃在复旦大学接受了早报记者专访,就当代女性主义运动的主要问题作了她个人回应。
已经71岁的克里斯蒂娃被认为是继西蒙·德·波伏娃之后最杰出的法国女思想家,她从不避讳自己是个女性主义者的身份,所以她也常常被归入当代女性主义思想家行列。以克里斯蒂娃为主要代表的女性主义越出了以往女性主义的思想界限,不再局限于女性主义的范围,而是以女性的“母亲身份”为典范,通过对一系列女性天才及卓越人物的历史分析,揭示人的个体及其不同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多重多元的异质性。于是,她接连为三位杰出女性立传,并收录在《女性天才系列》:《汉娜·阿伦特》、《美拉尼·克莱因》、《柯列特》中。在谈到她的《女性天才系列》时,克里斯蒂娃明白地指出:“诉诸每个男人或女人的天生才资,并不是低估历史的意义,而是试图超越女性的条件,就好像超越一般人的条件那样,超越生物学、社会和命定的界限;这也就是要强调主体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反抗各种决定因素的规定而创造出来的价值。”
1974年,克里斯蒂娃作为“左翼学生”代表来到中国,同行的有菲利普·索莱尔斯、罗兰·巴特、弗朗索瓦·瓦尔、马瑟兰·普莱耐。这段经历后来写进了《中国妇女》一书。2011年,她还来到上海,参加了《中国妇女》中文版在同济大学的首发式。
强调女性的
特殊性和个性
东方早报:你在复旦大学光华杰出人文学者系列讲座中,有一讲内容是关于阿伦特、克莱因和柯列特三位杰出女性的,你也为这三位女性分别作了传,其中《汉娜·阿伦特》已经在中国出版。通过这三部女性传记,你提出了一个“天才女性”的观点,这也是你的女性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在你看来,“天才女性”理论的现实意义在哪里?
克里斯蒂娃:汉娜·阿伦特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女性,她是犹太人,她学习哲学,一度想从事神学研究,她是海德格尔的恋人,而海德格尔和纳粹还有瓜葛。阿伦特到了法国之后,还差点被扔进集中营,后来她又到了美国。她之后又与海德格尔恢复来往。人们对她的误解首先是她没有跟海德格尔划清界限,其次是她与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使她遭受很多骂名。
在我看来,女性问题对所有的文明和文化都非常重要,在这个新千年尤其重要。我提出了“天才女性论”这个观点,首先是基于一个历史传统。“天才”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西方概念,当人们开始对上帝的信仰有所动摇和怀疑的时候,人就对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自信,而我们就会把那些最杰出的人称之为“天才”。这些杰出的人或者天才,几乎可以接近上帝,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那些巨匠。这些被神话的人或者天才,一方面能激励普通人超越自我,另一方面也掩盖了人自身的弱点,而基督教非常强调人的弱点和罪恶。
“天才”作为一个主题是西方人文传统的一部分。在这样一个传统下,这里的“天才”一般都指的是男性,不可能是女性。我提出“天才女性”这个观点,并写了那三本书,一方面也是希望女性,也包括男性,所有人都能超越自我;另一方面,在西方当代女性运动多年努力下,女性已经通向了自我解放的道路。但是在这些女性运动中,比较忽视个体性,仅仅把女性当作一个群体来对待,所以我用“天才女性”论来强调女性作为个体,她的天才,她的创造力在哪里!
东方早报:放在整个女性运动历史中,在你看来,当代女性运动处于什么状态?
克里斯蒂娃:首先回顾一下女性运动走过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这个运动开始于19世纪末的英国等新教地区妇女选举权运动。我这里特别要提一下1919年的“五四运动”,从那开始中国的女性也有自己的女性运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女性运动在全球女性运动中的位置。第二个阶段是,争取男性和女性平等的阶段,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就是西蒙·德·波伏娃和她的《第二性》,女性应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因为女性和男性拥有共通的人性。在这个方向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与这个阶段的西方女性运动有相似的地方,中国共产党颁布了很多关于男女平等的法律,也让很多女性进入领导阶层,或者也就是所谓的“女人要顶半边天”。我1974年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就特别关注中国女性在社会中的地位,我也在《中国妇女》这本书里写到了这段在中国的观察。第三个阶段是1968年的学生运动,伴随而来的是新的女性运动思潮兴起,大家开始讨论男女性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女性有哪些特殊的地方,女性的身体、女性的性经验和男性相比有哪些不同,女性的书写、艺术创作和政治思想等更广范围内,作为女性有何不同。从这个方面出发,我们可以走得更远。
今天的女性运动也是我所参与的女性运动,希望能在每个女性身上找到她们的特殊性和个性,女性对个性和特殊性非常的敏感,比如她们对时装的感觉。女性作为一个性别,她跟男性有何不同,还有女性个体有什么样的个性,这就与西方传统中的人道主义相遇,人道主义必定是建立在尊重每个人个性的基础上。
每个人的性别
是一种组合
东方早报:关于女性主义,公共讨论中经常纠缠于这样一个判断:女性到底是不同于男性,还是成为男性。你怎么看?
克里斯蒂娃:这两种倾向大致可以概括为同一性和差异性。但我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学家,在每个人身上都看到了两性的存在,这就如中国传统中所说的阴阳,女性身上也有阳,男性身上也有阴。但就我个人而言,我更倾向于男女的差异性,人类由男女组成,如果取消性别差异,大家都成为中性人,比如现在生物科技中所做的克隆人,那对人类文化可能是个灾难。文化需要两种性别的存在,需要我们每个构造不同的身体。所以我在那三本书(指阿伦特、克莱因和柯列特的三本传记)中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性别,我是克里斯蒂娃,在我身上大部分是女性特质,但我也有男性特质的一部分,所有这些综合起来就组成了克里斯蒂娃的性别。每个人的个性性别其实是一种组合,每个人的个性组合都是不同的,这其中就包含了每个人的创造力。所以我说,将来,我们更多应该去思考每个人的性别组合,而不是绝对地区分男和女,甚至把男女对立起来。
东方早报:男女性最大的差异就是生育。
克里斯蒂娃:这就要看你怎么看待生育问题。女性身上最特殊的地方是生育(能力),很多女性出于对男性地位的畏惧,常常把生育看成是额外的负担,把母性跟奴性画了等号,但我在母性上看到的是激情和爱。母性是社会最基本的联系,尤其是在这个没有宗教权威的社会里,如何去诠释母性是个问题。在宗教里,如何诠释母性有独特的话语,在宗教失去权威的情况下,我们还没有建立新的诠释话语去思考母性。所以,新的女性主义话语应该更多去关注母性的思考。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在两种文明里母性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中国文明,另一个是基督犹太文明,这两种文明中,母亲的位置特别重要。
现代女性运动更多
参与公共事务
东方早报:不可否认的是,现在的女性运动是作为思潮而存在的,它存在于学院中,跟公共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克里斯蒂娃:公共空间中,女性运动的讨论还不是很明显,尤其是在中国。第一个原因可能是,女性主义和女性运动的很多概念,在东西方是以不同的方式存在的,这是文化差异。西方所理解的个人和与之相关的自由精神,在中国的话语中的表述和价值都有不同。
但也不能说,学院之外就没有女性运动存在,它可能是以其他方式存在。比如我创立的西蒙·德·波伏娃奖(注:西蒙·德·波伏娃奖是一项表彰女性自由的国际人权奖项,2008年起授予为男女平等以及反对人权侵害而抗争的个人或团体。),奖项评委有30多人,来自世界各地。
举个例子,法国巴黎郊区前几年暴动,其中发展出一个女性运动,她们的口号是“既不做娼妇,也不做奴隶”。这是由巴黎郊区的阿拉伯妇女发起的,这些人被吸纳到西蒙·德·波伏娃奖执行评委里,这样她们就和世界的女性运动产生了联系,从她们自身经验出发思考世界女性运动。我们最近建议的西蒙·德·波伏娃奖的候选人是突尼斯的一些女性,她们在“阿拉伯之春”后,又面临着传统宗教势力的压制,她们又被要求戴上黑面纱等等,她们中的一些人就出来抵抗这种宗教压制。“既不做娼妇,也不做奴隶”运动的那些人就建议把奖颁发给这些突尼斯女性。
东方早报:所以女性运动不只局限于走上街头争取女性权益,女性运动其实应该更广泛地参与到社会公共事务中,是否如此?
克里斯蒂娃:我非常赞同这个意见。我有一本书《反抗的未来》,这本书也已经翻译成中文,在这本书中,我说,反抗是一种个人行为,是对个人过去的清算并重新开始。现在的女性运动越来越多的是做一些具体公共事务,而不只是为女性这个群体来呼喊,但同时,女性还是有走上街头的需要——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比如,前段时间,俄罗斯一个女子摇滚乐团因为对普京不敬而被逮捕,一些俄罗斯的女权组织就上街抗议要求释放她们。但当今女性运动更深层运动方式,是个人对社会事务的参与。
我来上海前,朋友建议我看最新一集的《007》,其中很多镜头都是在上海拍摄的。我家人对我说,你这几年几乎每年都去上海,跟007一样。在我看来,现代的女性运动是争取女性自由的秘密特工,女性运动的身份比较隐秘,我们的身份不是那么明显,却是在做一些具体的工作。新版的《007》跟以往最大差异是,邦德最后是用匕首结果了那个坏蛋,这是对传统的回归。我自己本身是一个从传统中来的女性主义者,但我知道怎么去利用现代手段做女性运动,比如媒体。所以,我是女性运动的詹姆斯·邦德。![]()
免责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凤凰网无关。其原创性以及文中陈述文字和内容未经本站证实,对本文以及其中全部或者部分内容、文字的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本站不作任何保证或承诺,请读者仅作参考,并请自行核实相关内容。
- 社会
- 娱乐
- 生活
- 探索
- 历史
湖北一男子持刀拒捕捅伤多人被击毙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7:02
04/21 06:49
04/21 11:28
频道推荐
商讯
48小时点击排行
-
706809
1女人心声:追求美丽是件痛苦的事 -
437124
2春天常吃10种蔬菜可帮你补足“阳气” -
431278
3美国华人圈屡现临时夫妻 专家:谈道德 -
386713
4姜培琳:从传奇超模到豪门CEO -
346637
5Gucci 2014米兰秋冬发布 -
272133
6普京绯闻女友时尚品味不输名媛 占领时 -
268855
7死亡真相:人在临死前10秒真实感受 -
203407
8肚脐形状辨疾病:哪种形状暗示有妇科病





















